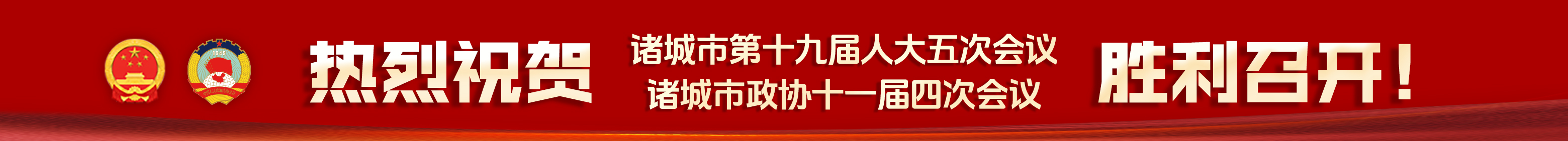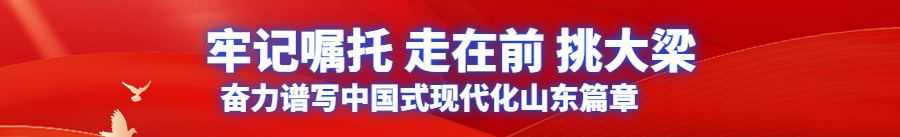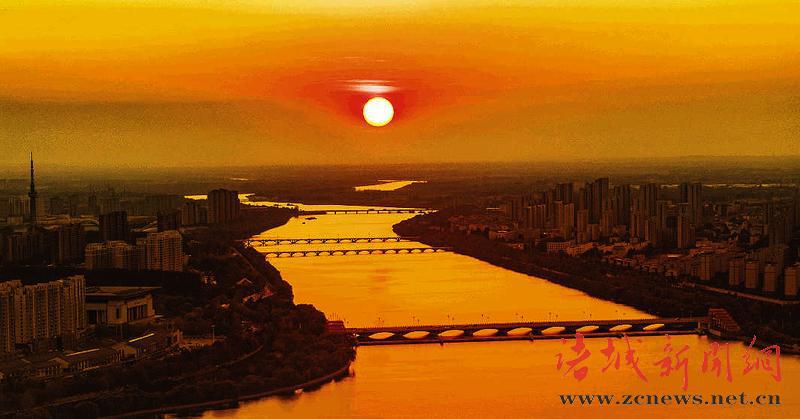臧家軍
“吃派飯”這個詞,,已從民間消失了30多年。現(xiàn)在提起吃派飯,,時下年輕人都很陌生,,而我們這一代人,卻是記憶猶新,,難以忘懷,。
吃派飯,主要是上個世紀(jì)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民公社時期的產(chǎn)物,。吃派飯就是由生產(chǎn)隊(duì)長或保管員安排某人到某戶社員家吃飯,,故名曰“吃派飯”。吃派飯,,是人民公社時期農(nóng)村習(xí)以為常的事,。
當(dāng)時能在大隊(duì)里吃派飯的只有三種人:公社干部、教師和盲人藝人,。那時上級有規(guī)定,干部,、教師到社員家吃派飯,,每天1斤糧票3毛錢。盲人是縣里組織的“盲人宣傳隊(duì)”,,他們不掙工資,,只靠演藝特長到各個大隊(duì)巡回演出,,一天3頓飯不用花錢和糧票,由所在生產(chǎn)隊(duì)按規(guī)定補(bǔ)助給社員糧食,。這樣,,吃派飯就形成了三條線。
第一條線主要是下鄉(xiāng)駐點(diǎn)幫助大隊(duì)開展工作的公社干部,,另外還有短期因公來大隊(duì)辦事的,。派干部飯,專挑選既干凈又會做飯的人家,,因干部為工作到大隊(duì)里來,,總得讓他們吃得舒舒服服,不然大隊(duì)干部便會沒面子,。然而,,公社干部大都很自覺,他們既不挑飯也不愿意麻煩社員,,除了駐大隊(duì)“點(diǎn)”的以外,,一般辦完事情就匆匆蹬著自行車返回公社。公社干部在社員家中吃飯,,通過閑談聊天,,社員家中的疾苦,張家長李家短,,都會了解得一清二楚,,工作起來就有針對性。
第二條線是單身在村小學(xué)任教的老師,,沒法自己做飯,,便只好由社員挨家挨戶輪著管飯。老師吃派飯一般單獨(dú)有一條輪換的線,,按生產(chǎn)隊(duì)的順序,,一戶一戶往下輪,時間長了便形成軌跡,,用不著生產(chǎn)隊(duì)里的干部去通知,,到時候該誰管飯他自家都會知道。上家和下家可以互通情況,,使飯食的花色變換,,以免太單一。每到飯點(diǎn),,由家長或孩子把老師領(lǐng)回家,。一家管一天,沒孩子上學(xué)的人家也要管,這是一項(xiàng)全村人的責(zé)任,。你家現(xiàn)在沒上學(xué)的,,不等于以后也沒有。教師吃派飯的質(zhì)量,,則要好于公社干部,。這并非農(nóng)家偏心眼兒,而是鄉(xiāng)下人講“實(shí)惠”,,誰都希望教師在學(xué)校里對自己家的孩子好,。教師通過在學(xué)生家吃派飯,能及時了解學(xué)生在家的情況,,家長也能及時知道孩子在學(xué)校的表現(xiàn),。這樣教師和家長互相通氣,對學(xué)生的教育就有了針對性,。
第三條線是盲人到村里宣傳,。盲人是縣里組織的宣傳隊(duì),吃飯沒那么多講究,,不管到了哪個大隊(duì),,找個生產(chǎn)隊(duì)隨便安排戶社員家吃飯就行。
上世紀(jì)六七十年代,,社員家日子過得都不富裕,,除了逢年過節(jié)能吃幾頓“面飯”以外,平日里大都以地瓜(干)為主,,玉米面餅子也很少吃,,就的是咸菜,吃炒菜的機(jī)會很少,。即便如此,,不管輪到哪家,管飯主人大都盡心做一頓“好飯”,。這是怕公家人吃不好,,更怕飯菜不好一旦傳出去,糟蹋了自己家的“名聲”,。那時的所謂“好飯”,,無非是蒸幾個餑餑,搟頓面條,,包頓包子,,或者是包頓水餃等,極少有酒,。一般都是男主人陪餐,,女人,、孩子不上桌子。等公家人吃飽喝足以后,,老老少少才能吃他們剩下的飯菜解解饞。
那時候,,因日子過得太苦,,吃派飯還鬧出不少笑話。在昌城公社曾發(fā)生過這樣一件事,,有一公社干部到某大隊(duì)檢查工作,,中午和老師一起到社員家里吃飯。女主人煎了一盤黃尖子魚端上桌,,主人家6歲的小男孩,,就在房門口掀起門簾緊盯著炕上飯桌上那盤黃尖子魚。女主人悄悄地對男孩說,,你不要看了,,人家就給你留著個了。小男孩不放心,,不時地掀起門簾向里面炕上瞅瞅,。農(nóng)村有個風(fēng)俗,一般會留一條魚在盤子里,,寓意年年有余,。男主人熱情好客,看到最后一條魚在盤子里半天沒有人動,,就熱情地讓著公社干部和老師吃魚,。盛情之下,公社干部把最后一條魚用筷子夾起,,正在門簾縫里瞅著的小男孩不干了,,“哇”的一聲大哭,掀開門簾突然沖進(jìn)炕前喝道:“你不要吃了,,那個魚是我的,!”
從上世紀(jì)70年代中期開始,派飯質(zhì)量逐漸提高,,管飯的人家開始給公家人點(diǎn)兒“小酒”,。然而不管飯菜好與壞,也不論有沒有酒,,公家人付費(fèi)的標(biāo)準(zhǔn),,都還是每天1斤糧票3毛錢。吃派飯所不同的是公社干部和教師要到管飯的人家里吃,,盲人宣傳隊(duì)則由管飯的人把飯送到他們的臨時住處,。
在我的記憶里,社員管派飯都很熱情,歡迎工作隊(duì)員,、教師到他家吃飯,,都算好了日子,哪天到誰家,,哪天輪到自己家,。于是,輪到自己家的,,沒油的去借油,,沒菜的準(zhǔn)備菜,到街上去換豆腐,,都千方百計(jì)地準(zhǔn)備準(zhǔn)備,,就怕丟了自己的臉面。
在上世紀(jì)六七十年代,,我們家就管過不少派飯,。我模模糊糊地記得,上世紀(jì)60年代中期,,“四清”工作隊(duì)進(jìn)駐我們史家溝大隊(duì),。我們大隊(duì)是四面環(huán)山的一個小山村,抬頭看看長長天,,低頭看看石頭山,。那時經(jīng)濟(jì)不發(fā)達(dá),社員家日子過得都很苦,,常年以地瓜(干)當(dāng)家,,玉米面也很少,白面更少,,逢年過節(jié)才能吃上頓面食,,甚至到了青黃不接時連地瓜干也吃不上。盡管這樣,,家家戶戶都還掙著管工作隊(duì)員的飯,,認(rèn)為誰家能管工作隊(duì)員的飯,這是誰家的榮耀,。工作隊(duì)員輪到我們家吃派飯正是青黃不接時,,家里似乎什么也沒有,母親向我大娘家借了一瓢面,,向我三嬸家借了幾個雞蛋,。母親用白面摻上地瓜面烙了幾張餅,炒了兩個菜:一個韭菜炒雞蛋,,一個清炒茼蒿,。母親囑咐我,,吃飯時,你和弟弟到街上去耍著,,估摸著你父親和工作隊(duì)的人吃完了,,你和弟弟再回來。等我們回來時,,盤里的菜早已底朝天,,好在笸籮里還剩了兩張餅。我和弟弟就拿起餅不管不顧地大口吃起來,。
到了上世紀(jì)70年代初,我們家管派飯就明顯多起來,,因我父親是生產(chǎn)隊(duì)長,,書記又和我們一個生產(chǎn)隊(duì)。每當(dāng)有公社干部來大隊(duì)檢查指導(dǎo)工作,,書記就讓我父親領(lǐng)著他們回家吃飯,。長遠(yuǎn)熟了,有時還不等書記說,,來的干部就直接點(diǎn)名要到我們家吃,。父親和母親都熱情好客,不管是誰到我們家吃飯,,就是家里東西不便,,母親也東取西借,盡量做些好吃的讓他們吃,。再說,,父親也好喝兩口,也就從來不推脫,。那時,,雖說是生活條件有些好轉(zhuǎn),但過慣了窮日子的母親,,平時也不舍得父親拿3斤地瓜干2毛8分錢去換斤諸城散白酒喝,,只有家里來了客,或有吃派飯的,,父親才能美美地喝上兩盅,。
在我們大隊(duì),公辦教師吃派飯,,從上世紀(jì)60年代末一直延續(xù)到70年代末,。教師調(diào)進(jìn)調(diào)出三四個,直到調(diào)來一個成了家的女教師,,才不再吃派飯,。
1975年的春天,,我也實(shí)實(shí)在在地吃了一回派飯。那是我上高三那年,,我們班的同學(xué)到西響水大隊(duì)接受貧下中農(nóng)再教育,,男同學(xué)都被分去水庫建設(shè)工地扛石頭。吃中午飯時,,我和另一位男同學(xué)被派到一位老大娘家,。記得老大娘在當(dāng)門里安了一張飯桌,讓我們一人坐一邊,。老大娘在桌上放了一碗辣菜咸菜,,又從鍋里拿出4個煎餅放到桌上的笸籮里,我們一人拿起一個就吃起來,。老大娘坐在鍋門口望著飯桌,,當(dāng)老大娘看到我們把第二個煎餅吃到還剩三分之一時,就又餾上了倆,,我們又一人一個吃起來,。老大娘見我們把煎餅又吃到還剩三分之一時,就又餾上了倆……那時,,我們是十八九的小伙子,,是吃石頭都能化的年齡,但看著老大娘既怕我們吃不飽又舍不得多餾的情景,,實(shí)在不忍心讓她為難,。當(dāng)她反復(fù)餾到第4次時,我和同學(xué)對望了一下,,撕開一個煎餅,,給老大娘留下一個,老大娘這才不再餾了,。
再次吃派飯,,是公社改鄉(xiāng)鎮(zhèn)、大隊(duì)改村后的1984年秋天,。那時,,我在壽塔鄉(xiāng)中心小學(xué)負(fù)責(zé)業(yè)務(wù),因壽塔鄉(xiāng)是剛剛從郝戈莊公社分出來的,,中心小學(xué)(原來的前壽塔小學(xué))沒有伙房,,我們就根據(jù)學(xué)生花名冊,輪著到學(xué)生家吃派飯,。這時經(jīng)濟(jì)條件明顯好轉(zhuǎn),,不管輪到哪個學(xué)生家吃得都很好。淳樸實(shí)在的學(xué)生家長們,,都盤算著日子,,數(shù)算著老師什么時候輪到自己家,,好提前做準(zhǔn)備,變著法兒做有特色的飯菜給老師吃,。有個姓林的學(xué)生家長,,在我們?nèi)コ燥埖念^一天,早上早起來到坡里下套子套野兔,,白天還扛著獵槍(那時公安部門還沒有收繳獵槍)打了一整天,。我們?nèi)ニ页燥埬翘欤瑥脑绲酵碜郎铣吹?、燉的全是野兔肉,。他看到我們吃得津津有味,很是自豪,,說:“我數(shù)算著你們今天輪到我們家,,就想搞點(diǎn)你們平常吃不到的東西。昨天一早我就去下套子,、打野兔,你們還真是有口福,,想不到一天竟打了4只,。”像姓林的這樣的學(xué)生家長很多,,他們憨厚樸實(shí)的臉,,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里。
30多年過去了,,吃派飯的事離我們漸行漸遠(yuǎn),,但回想起來仍如昨日。吃派飯雖然是時代的產(chǎn)物,,但是它卻拉近了干部和群眾,,老師和家長,城里人和鄉(xiāng)下人之間的距離,。增進(jìn)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,。是一種很好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、交往形式,。
(作者系中國報(bào)告文學(xué)學(xué)會會員,,山東省當(dāng)代文學(xué)院院部委員)
1 條記錄 1/1 頁